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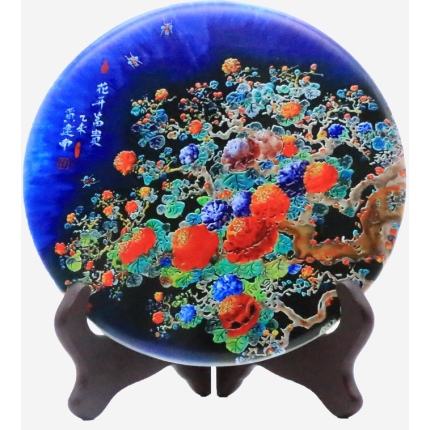
据新华社,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月30日宣布,对伊朗商人穆罕默德·侯赛因·沙姆哈尼控制的航运网络实施制裁,涉及50多个实体和个人以及50多艘运油船和集装箱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侯赛因控制的航运网络将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石油衍生品以及其他货物运至世界各地。侯赛因的父亲阿里·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曾于2020年受到美国制裁。当天,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将参与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与运输的2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将10艘船只列为冻结资产。
内部经济停滞、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企,外部冲突频仍、屡遭制裁,使伊朗成为“失败国家”的典型代表。作为不折不扣的能源大国,以及人口和国土面积上的区域大国,伊朗的发展条件并不差,但伊朗何以至此?
在诸多的因素中,伊朗独特的神权共和政体往往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解析了伊朗独特的神权共和政体结构及其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时代的运作过程。文章指出,神权共和政体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运行方式,因此,特定政体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伊朗的现代化困境与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政权未能确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深层次改革屡受制约有关。云开全站Kaiyun平台
本文反思了“历史的终结”叙事,指出“自由民主”并非普世通解,一国治理体系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腐败并激励经济创造。
自从今年6月“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这一国家再次密集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在战力不足背后,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IMF的数据,2024年,经通胀调整后的伊朗人均GDP仅为约4500美元。此外,伊朗已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根据提供伊朗货币里亚尔实时汇率网站Bonbast的信息,2015年,1美元可兑换4万里亚尔;2025年6月,公开市场汇率达550,000里亚尔兑1美元,贬值超90%。这意味着伊朗的经济秩序已经基本崩盘。在失业率方面,伊朗统计中心所披露的总体失业率高达7.6%,其中青年(15-24岁)失业率为20.2%。鉴于伊朗约有三分之二人口低于35岁,伊朗的失业状况非常严重。伊朗还陷入了长期的人才流失问题中。2024年,伊朗赴外留学学生数量创历史新高。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最近声称,高达80%的学生正在考虑移民,而其科学部长则指出,过去几年里已有25%的大学教授离开。
伊朗坐拥16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以及9060万人口,是不折不扣的区域性大国。伊朗的自然资源禀赋优越,据统计,伊朗石油储量高达1580亿桶,位居世界第四,天然气储量33.9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伊朗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既然有如此优越的发展条件,伊朗为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停滞不前?
在诸多可能的原因当中,伊朗独特的神权共和体制往往备受关注。在西方媒体中,将伊朗失败原因指向伊朗专制神权政体的声音占据主流。这些分析往往沿用“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将伊朗的“神权专制政体”视作伊朗的“原罪”,不仅以此解释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也认为它造就了伊朗“邪恶轴心”的地位。本文对伊朗这一独特政体及其确立后的运作过程分析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政体具有一定的现代元素,与想象中的神权专制政体并不等同。神权共和政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伊朗精英有效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和谋求发展的一种创造性发明。伊朗现代化停滞更多与这一政体的保守化运作有关。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并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独具一格的伊斯兰共和政体。这一政体的典型特征是由顶层伊斯兰教士集团的“监护”地位,和世俗化的民选政府组成的二元结构。
在宗教政治部分,法基赫,即教法学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利中枢。在十代伊玛目隐遁时期,法基赫作为穆斯林的领袖代行伊玛目的一切权力。宗教最高领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有宣战和停战的权力。他还有权任命“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任命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总统候选人和根据最高法院和议会的提议任免总统。法基赫由选举产生的“专家会议”选举产生,后者是由86名成员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成员由选民根据各省市的人口比例从宗教法学家中选举产生。
哈梅内伊于1989年上任,为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其身后照片为是他的老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图源:网络)
法基赫行使监护权的关键机构是“监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共12名成员,除半数是由法基赫选任的高级教士外,其余由议会在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中选任。“监护委员会” 旨在确保议会的立法不得违背国教和宪法的准则,因此在实际上享有立法否决权。为了保障这种特权不被议会架空,宪法规定,如无“监护委员会”,议会“不具有任何合法地位”,议会开会选任“监护委员会”成员时除外。由任命产生的“监护委员会”实际上起到法基赫的辅佐机构和上议院的双重作用。监护委员会有权审订“专家会议”、云开全站Kaiyun平台“议会”和总统的候选人名单。1988年2月,霍梅尼又下令成立了由总统、议长、总理(1989年后取消)、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霍梅尼办公室主任、宪法监护委员的6名成员及政府有关部长组成的“权益委员会”(The Expediency Council),负责对议会和监护委员会之间存在分歧的法案最终审定。
在民主政治部分,伊朗总统和议会皆为选民选举产生,但宪法特别规定总统和议员就职前必须宣誓捍卫伊斯兰教、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议会的正式名称是“伊斯兰协商议会”,凸显其伊斯兰性质和咨询作用。议会实行一院制。任期4年。如前所述,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监护委员会”。根据宪法,总统是行政部门首脑,负责协调政府三权,任期4年,一人最多只能任两届。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是仅次于法基赫的职务,但总统不掌握军权。伊朗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效忠于最高领袖。
此外,总统权力的行使需要在最高领袖的“监护”下进行。这表现在,最高领袖及其领导下的监护委员会有权对议会、总统候选人进行审定;最高司法机关仍由领袖领导。并且,由于总统没有军权,这使得总统权力的行使大受制约。因此,最高领袖既是国家的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
从结构来看,伊斯兰共和政体是以传统神权政治为主,同时兼具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些现代元素的半现代政体。但它的运作模式实际上与最高领袖的实际威望、个人风格,以及精英内部的派别政治高度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霍梅尼作为开国领袖,凭借着自身克里斯玛气质和强硬的政治手腕高度介入世俗政治,对反对派进行镇压。因此,一般认为这是伊朗的政权巩固阶段。1989年,霍梅尼病逝,总统哈梅内伊被专家会议推选为领袖。哈梅内伊并不是具有较高宗教权威的大阿亚图拉(高级什叶派神职人员),其自身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可与霍梅尼相比,因而更多依靠和总统建立政治联盟的方式来推进政策,该政权对重新寻找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需求也更高。
总的来说,这一“混合政体”有几个优势:第一,相比较君主制下权威集中于君主,伊斯兰共和政体下的权威集中于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组织;因此,其包容性较君主制更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位置;第二,该政体对民主政治的吸纳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发声,从而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第三,最高领袖与行政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为行政首脑治理国家创造了一定空间。这使得伊朗伊斯兰共和政体成为极具适应性和韧性的政治结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其现代化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在霍梅尼时期,国家的重点是巩固政权和应对“两伊战争”等外部危机,国内经济高度国有化。进入哈梅内伊时期后,伊朗着力改革发展经济。在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1989-1997年),伊朗构建了以“务实派”人士和“非中坚保守派”分子为主的内阁,推崇技术官僚治国。在经济方面,确立经济自由化的方针,主张利用国际分工和外国资本发展民族经济,恢复国内私人资本的投资信心,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从中斡旋减少保守派的反对,对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期间伊朗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改善。在拉夫桑贾尼之后,哈塔米继续了其政治遗产,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甚至提出了宗教民主化主张;对外通过“文明对话”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到了第二任期,哈塔米改革已经因遭遇保守派的阻挠趋于停摆。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标志着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的失败与保守派势力的回归。内贾德更加强调社会公正,经济政策趋于保守。此后,鲁哈尼(温和派)、莱希(强硬派)和佩泽希齐扬(温和派)轮番登台。
Azadi Tower也被称为自由塔,其圆形底座代表了古代波斯建筑,特别是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圆形坟墓;塔顶呈方形,代表了伊朗的现代和伊斯兰建筑。在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这座塔是许多抗议活动的场所,如今它仍然是代表伊朗人民希望、坚韧、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图源:ArchDaily)
在改革派与保守派反复拉扯的进程背后,是伊朗在现代化进程走到一定程度后,其政体遭遇越来越大的内部张力的事实。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进而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实现了一定程度现代化的国家,要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需要更大程度地激活社会的力量。但是,这些天然地与以神权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逻辑相悖。教士阶级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与社会大众要求分享权力和财富之间形成张力。这一张力在一些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经济自由化与“军-经复合体”的矛盾。在伊朗,主要产业命脉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护持。这一传统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霍梅尼借助其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公正的分配”的需要。然而,这逐渐演变成教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教士阶级需要借助军队的力量维护其统治(并且双方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些经济利益则是教士给予军队的回报。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构建起一个较为庞大的“经济帝国”。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经济的20%。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35%。世俗政权推进经济自由化,必然会与“军-经复合体”,从而教士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伊朗总统鲁哈尼曾在2017年4月会见伊朗经济学者时曾抱怨,“伊朗《宪法》第44条政策是为了将经济交给人民和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掌握在‘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移交给‘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政策对“军-经复合体”的影响,本质上是政治经济改革危及了制度型腐败生长的基础。
第二,向外输出革命与谋求国内发展之间的矛盾。教士阶级为了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强化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对外强化伊斯兰革命输出。大量资金被用于支持分布在中东地区对抗以色列的伊斯兰革命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胡赛武装等。这进一步占用了本应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在国际社会上,伊朗的激进革命输出行为引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制裁,使伊朗陷入更加孤立无缘的境地。然而,吊诡的是,西方的经济制裁间接给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体制内”群体拓展经济版图提供了机会。不少伊朗人为了生存,除了依附于“体制”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有赖于一定程度的集权,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面对上文提到的这些内部张力,伊朗既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来弥合分歧,也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将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关系向制度化的方向调整,而是采用消极的“调和政治”。在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的40年来,他主要靠灵活的政治手腕来平衡国内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力量,尤其是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来协调国内各派,实现国家权力在少部分精英内部的再分配。其结果是,伊朗的合法性转型之困加剧了政策碎片化、行政低效,最终使得国内经济停摆。这也使得伊朗在参与国际事务中以“出尔反尔”著称,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通过对伊朗政体,以及伊朗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政体本身并不构成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不断炮制自由民主乃“历史终结”的叙事,刻意强化基于政体形式差异的意识形态对立叙事。伊朗的经验表明,通过对神权政体的创造性设计,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伊朗社会经济发展的。对比来看,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也未必成功。在地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方面,国家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起点、路径和所遇到的困难有所不同。“自由民主制”并非“历史的终结”。不少西方媒体刻意强化基于政体差异的意识形态对立,这既对包含伊朗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利,又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
第二,辩证看待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看,伊朗的神权可以与世俗国家中的意识形态相比照。意识形态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既能发挥整合社会、凝聚共识的正面功能,也可能因排他性而阻碍改革。伊朗神权政体背后的什叶派第十二伊玛目教义在国家建构中曾具有强大凝聚力。但随着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兴起,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张力日益严重。伊朗作为历史悠久且屡遭外侵的国家,在民族身份建构上具有强烈诉求。伊朗对其民族意识形态应进行更加务实的重新阐释,以适应新的社会条件。
第三,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政治制度能否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应调整非常重要。伊朗的经验表明,神权共和政体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更多要看能否根据现代化的要求进行调整。规则并不是不可改的。比如说,从理论上讲,伊朗最高领袖应由“效法的源泉”大阿亚图拉担任,但1989年霍梅尼病重时,当时国内的几位大阿亚图拉或年事已高或不具备政治家素质。为了使哈梅内伊顺利继位,霍梅尼主持了宪法修改,规定最高宗教领袖不必是大阿亚图拉,从而为最高领袖的政治化铺平了道路。伊朗陷入的困境与其政权未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确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深层次改革屡受制约有关。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成败与政权稳定与否,在于其制度是否包容、治理是否良善。西方的“自由民主”并非普世通解,这已经能从诸多陷入政治失序和发展停滞的国家中得到印证,伊朗的邻国伊拉克就是一个很好例子。衡量一国治理体系优劣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构建健全的问责机制、遏制腐败,并激励经济创造。